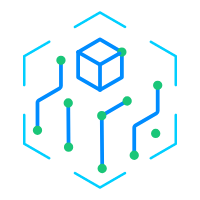曹寅:荷属东印度的缝纫机为何被用来标示身份和地位?
曹寅:荷属东印度的缝纫机为何被用来标示身份和地位?
曹寅:荷属东印度的缝纫机为何被用来标示身份和地位?,家里缝纫,缝纫机乐队大鹏,手工缝纫本缝纫机在19世纪末被引入荷属东印度群岛(即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在殖民地精英的想象中,缝纫机作为现代技术一方面能够帮助印尼女性挣脱家庭的束缚,成为有自主谋生能力的劳动者;另一方面缝纫机也可以提高纺织业的劳动效率,节省劳动力和成本。然而,这种被赋予了现代、进步、效率内涵的技术工具却在印尼成为富裕家庭的摆设和装饰品,被用来标示身份和地位。本章将展示殖民地精英对于现代技术的认知与技术在殖民地实际应用之间存在着的巨大偏差,以及这种偏差所反映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荷属东印度社会内部的张力。
争夺亚洲贸易航线世纪上半叶,荷兰东印度公司与葡萄牙王国为争夺亚洲的贸易航线爆发了一系列的冲突。荷兰人最终打败了葡萄牙人,并控制了苏拉特、马六甲、科伦坡等重要贸易据点,由此开启了荷兰在亚洲贸易的黄金时代。位于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东北部的巴达维亚,则是荷兰东印度公司亚洲贸易网络的中心。
到了18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竞争中渐落下风,最终于1799年宣布解散。相应地,荷兰人在亚洲的活动也逐渐从贸易活动变为依靠攫取印尼的自然资源和剥削印尼土著获利。这一时期的巴达维亚则从一个贸易中心转变为了荷兰向爪哇内陆和印尼其他岛屿扩张的桥头堡以及进行殖民统治的行政中心。
自19世纪开始,印度尼西亚由荷兰殖民部直接管理。荷兰人通过干预地方土著王国的内政、挑拨不同王国之间的关系、委任土著苏丹间接统治、对反抗者进行军事征服和等方式试图不断巩固其在印尼的殖民统治。 康奈尔大学历史学家埃里克·塔格里亚科佐(Eric Tagliacozzo)认为,荷兰对于整个印度尼西亚的殖民征服由于受到技术和经济能力方面的限制以及亚洲跨境族群的直到20世纪初都没有完全成功。
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学术界在研究荷属东印度的历史时,倾向于将研究对象简单二分为荷兰殖民统治阶层与印尼土著。绝大多数研究关注的是荷兰殖民官员的个人经历、殖民政府的政策与制度变迁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商人的事业。
在这些研究中,印尼土著以没有主体性的形象出现在背景中。荷兰学者范卢尔(J C van Leur)在1930年代就注意到了荷属东印度历史书写中存在的这种欧洲中心观。他认为荷属东印度的历史学家们是以双重视角在书写印尼历史——在书写荷兰人来到印尼之前的历史时,他们采用的是本地视角;但当书写荷属东印度历史时,他们就自然而然地放弃了本地视角,而代之以荷兰殖民官员的视角。
范卢尔的批评在当时并未引起关注。直到1960年代约翰·斯迈尔(John Smail)才对范卢尔的观点做了呼应。斯迈尔以夜间小道行车做比喻,认为受欧洲中心观影响的历史学家在研究荷属东印度历史时就如同开夜车时只看着车灯照亮的那部分道路。那些没有被车灯照亮的景色正犹如那些非殖民地精英们的历史一样,都遗失了。范卢尔和斯迈尔都强调要跳出将荷兰殖民精英放在叙事和观察中心的欧洲中心史观,从当地土著的角度去尝试给出不一样的历史叙事。
表面看来,范卢尔和斯迈尔要求超越欧洲中心史观的呼吁是与赛义德对“东方主义”的批判相呼应的。然而简·泰勒(Jean Taylor)敏锐发现将赛义德的理论引入荷属东印度历史研究中来可能不仅不会为印尼土著带去更多关注,反而会将学者们的注意力重新拉回到西方。赛义德在其《东方主义》一书中认为西方想象和构建了一个停滞和落后的“东方”,并通过这种想象来强化其殖民扩张的合法性。
简·泰勒于1983年出版的《巴达维亚的社会世界》(The Social World of Batavia: Europeans and Eurasians in Colonial Indonesia)一书实践了范卢尔和斯迈尔倡导研究印尼当地社会的主张。泰勒认为巴达维亚的社会结构并不能被简单二分为荷兰殖民统治者和被压迫剥削的印尼土著。
17世纪之后来到印尼的西方殖民者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群体。他们不仅仅只是荷兰人,还包括了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等许多欧洲其他国家的族群。这些西方人大多数也并不是什么殖民统治者,而是商人、士兵、工程师、科学家、探险家、无业游民等。同理,所谓的印尼“土著”也包括了印度人、华人、日本人、阿拉伯人等来自亚洲各地的移民。泰勒认为这些族群之间的长期交融使得巴达维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既不是对荷兰本土的单纯复制,也与印尼本土不同。
巴达维亚多元文化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西方男性与欧亚混血女性的通婚。由于在19世纪前极少有欧洲女性来到印尼,因此定居在巴达维亚的欧洲男性选择与当地权势家族的女性通婚。在这种婚姻中出生的混血女性被认为具有两种资源——一方面她具有白人的血统;另一方面她又拥有当地权势家族的资源——所以她们成为新来到印尼的荷兰殖民官员的理想婚姻对象。通过研究这种由荷兰男性与欧亚混血女性组成的家庭社会网络及其在巴达维亚强大的政治经济影响力,泰勒展示了分析殖民地时期印尼社会文化的新范式。
到了19世纪,现代化技术和设备逐渐出现在印尼,并带动了当地多元社会的深刻变革。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家鲁道夫·姆拉泽克(Rudolf Mrazek)发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线性发展观念开始渗透到印尼社会的方方面面。当时印尼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对现代技术抱持着乐观的态度,认为使用诸如铁路、蒸汽船、光学仪器、电话等技术可以帮助印尼走出愚昧落后迷信的黑暗时代,使之发展为一个现代国家。
在这个现代印尼国家中,欧洲人与印尼土著能够快乐和富足地共同生活。然而姆拉泽克指出,人们对于技术和现代性的痴迷与期待并没有弥合印尼社会内部的差异,反而加速了印尼多元社会的瓦解,并加深了荷兰人与印尼人、权贵与平民之间的隔阂。到了荷兰殖民统治末期(1940年代),现代技术已然成了为荷兰和印尼权贵们服务,巩固其既得利益以及为其控制和剥削基层社会的工具。
如果说泰勒向读者展示了近现代印尼多元社会的兴起及其主要特征,那么姆拉泽克则描绘了这个多元社会在现代性的影响下是如何异化和分化的。姆拉泽克在泰勒研究视角上所作的进一步探索和创新标志了荷属东印度史研究的转向。学者们不再满足于讨论印尼社会内部的性别、家庭、族群等议题,而是试图将现代性对于印尼多元社会的影响与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复杂互动联系起来。本章借鉴了姆拉泽克的研究视角,尝试以缝纫机这一现代技术工具为例,揭示印尼多元社会在与现代性遭遇后发生的阶层与族群的异化。
缝纫机可能是近代以来最早被规模化生产并在世界范围内销售的工业消费品。在缝纫机的全球扩张进程中,美国的胜家缝纫机公司(Singer Sewing Co )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据统计,1912年美国家庭使用的缝纫机中有60%都是由胜家生产的,而在世界其他地区,胜家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惊人的90%。
胜家公司由美国发明家艾萨克·辛格(Issac Singer)和律师爱德华·克拉克(Edward Clark)成立于1851年,专门生产和销售家用缝纫机。到了1860年代,胜家公司开始在英国设厂,并开启了海外市场的扩张。安德鲁·古德里(Andrew Godley)发现胜家公司占领海外市场的主要策略是其直销体系和售后服务。胜家将其英国市场划分为若干固定区域,每个区域都设有销售点。销售点的专职销售经理定期挨家挨户地咨询顾客需求。对于购买了胜家缝纫机的顾客,工人则会提供每周的上门维护服务。这种销售方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1875年胜家在英国卖出了3万台缝纫机,10年之后达到了9万台。
与此同时,胜家公司也将注意力转向非西方世界。由于家庭缝纫机对于基础设施的依赖度较低(不需要电力或天然气),而大多数基础设施不完善的非西方地区又有着需求不断增长的中产阶层,因此胜家公司认为诸如非洲、奥斯曼帝国、东南亚等地将是其产品的潜在市场。在向亚洲和非洲客户推销其缝纫机的广告中,胜家公司将其缝纫机称为“文明的先导”。
这句极具“东方主义”偏见的广告具有双重意涵:一方面,去往亚洲和非洲的西方人需要带着缝纫机同行。因为亚非地区充斥着不文明的野蛮穿着,因此在彼处的西方人需要缝纫机缝制的现代衣物来彰显自身的文明与进步。另一方面,亚非当地的土著因为贫穷野蛮落后而往往衣不遮体。这些土著需要通过购买和使用缝纫机来学习文明的穿着和礼仪,从而帮助其社会进入文明的阶段。
缝纫机最迟在1880年就已经出现在了荷属东印度。泰勒从荷兰皇家东南亚和加勒比研究所(Royal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and Caribbean Studies)收藏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荷属东印度家庭日常照片中分析了缝纫机在当地所特有的社会内涵。她认为缝纫机在荷属东印度所呈现出的社会属性要远远大于其功能属性。在西方世界,家用缝纫机往往是与其缝纫衣物的功能直接相关的,然而在荷属东印度,缝纫机却更多的是一种展示品,用来标示使用者、拥有者的社会身份、性别以及族群的阶序特征。
自照相技术被引入印尼之后,印尼权贵和中产阶层都对其趋之若鹜。一般中产阶层会去照相馆拍照,其背景道具则是照相馆所提供的家具、花瓶和其他装饰品。富有阶层的家庭则会选择雇用专业摄像师到自己家中来定制化拍摄。一般而言,家中拍摄的首选场景是在屋前的花园或者草坪,主题则大都是男女主人与其子女以及亲朋好友的聚会。
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东印度家庭来说,聘请照相师来家中拍出的照片主要用于展示目的,比如寄给荷兰的亲朋或者放置在家中显眼位置,因此出现在照片中的物件是屋主人精心挑选出来以用于呈现其身份地位和智识品味的。在当时印尼富裕家庭照片中频繁出现的缝纫机、时尚吊灯和进口厨房用具等现代物件表明这些家庭希望通过上述物件被外界视作是“现代”和“文明”的。围坐在缝纫机旁的印尼女性仆人则表明了家庭成员的地位与分工——操作缝纫机的体力劳动需要由地位较低的土著来完成,而女主人则是负责监督仆人的劳动并享受仆人劳动的果实。
象征着“现代”与“文明”并因此而被用来展示的缝纫机却交由“未开化”的土著女仆操作,这种看似自相矛盾的安排显示了现代技术在殖民地社会的微妙处境。对于缝纫机的发明者来说,这种机械装置是用来帮助提高缝织效率以及减少劳动力成本的。然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印尼,当地的劳动力既充沛也廉价,富裕人家几乎都雇用有四至六个仆人打理家务,因此也就并不存在用相对昂贵的技术产品替代人工劳动的条件。实际上,缝纫机在印尼富裕家庭中的主要功能并非节省劳动力成本或者提高缝纫效率,而是与当时荷兰社会对女性的期待以及中产家庭女性想要展现自身地位的诉求息息相关的。
在19世纪末的荷兰,专门针对女性读者的时尚杂志非常热销。艾尔斯贝斯·舒尔腾(Elsbeth Locher Scholten)发现当时荷兰时尚杂志的主题之一就是强调使用缝纫机进行缝纫和针织对于提升女性魅力的重要性。一些杂志还开辟了专栏介绍各种服装裁剪教程和模板。对于那些打算去印尼生活的荷兰女性,设在海牙的荷兰殖民地女校(The Colonial School for Women and Girls)甚至专门开设缝纫课程,以便使她们能够在印尼监督和指导土著仆人进行缝纫工作。
这种将缝纫机和缝纫技术与现代女性形象联系在一起的宣传促进了缝纫机在印尼的热销。而当那些来到印尼定居的荷兰女性购买了缝纫机之后,她们又热衷于将这种技术通过照片展示给自己的亲朋好友以炫耀其在殖民地所享受的特权生活(一方面,她们可以与荷兰母国的女性一样拥有现代技术;另一方面,她们还享受众多仆人的服务而不用亲自动手去操作这些技术设备)。
对于印尼基层社会的女性来说,缝纫机的出现则给她们提供了新的机会与平台。在19世纪前,绝大多数印尼女性都依附于自己的父亲或者丈夫,并以务农为生。19世纪下半叶荷属东印度的经济发展带动了城市化进程。大量印尼女性开始进入城市寻找工作,其中的绝大多数成为城市富有家庭的用人。一方面,在雇主家中学到的使用缝纫机的知识使这些基层女性拥有了独自谋生的技能,让她们可以不再依靠父权家庭。不过另一方面,这些基层女佣在雇主家中始终处在不平等的位置,她们的薪水非常微薄,雇主对她们的歧视更是无处不在。
值得注意的是,缝纫机本身在成为印尼中产及权贵阶层用以标识自身身份的工具的同时,由女仆操作缝纫机所生产出的织物也成为身份标识物。缝纫机缝制出的带有各式花纹图样的窗帘、被套、桌布常常被用来显示家庭的审美情操、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生活在印尼的荷兰女性习惯于在家中穿着印尼传统的娘惹衫,只有外出参加正式活动时才会穿着西式女装。
除了富有家庭之外,专门缝制衣物的制衣厂也开始在19世纪末使用缝纫机。自1870年起,荷属东印度殖民政府逐渐放开了限制私人资本的法规,使得印尼的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私人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建设、种植园、矿产以及旅游度假等领域并带动了城市化进程。随着现代市镇的兴起,诸如石油化工、工程建筑、银行、教育、公务员等行业也随之出现,并对劳动力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些现代行业要求劳动力在观念和身体上被同时规训,以适应资本主义管理和生产效率最大化的需求。
这些在城市现代行业中工作的印尼人成为20世纪初印尼的白领阶层。荷兰莱顿大学历史学家舒伯特·诺德霍尔特(Schulte Nordholt)认为荷属东印度殖民政权的延续既要依靠这些白领工人的专业性工作,又取决于这些白领工人是否将荷兰视为他们汲取现代性的源泉并加以模仿。换句话说,荷兰人维持其殖民统治的基础就在于合理引导印尼人想要变得更加现代的欲望。
纽约新学院的人类学家安·劳拉·斯托勒(Ann Laura Stoler)将这种引导称为“欲望教育”,并指出在殖民当局与资本联合下,殖民地白领被“教育”和“引导”为资本包装下的现代性的“消费者”。将消费主义逻辑内化为了自身欲望的白领劳动者们不再关注殖民主义带给他们的结构性压迫和歧视,而更多的是去追求与荷兰人相同的现代生活方式。
在本章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以缝纫机为代表的现代技术在印尼发生了内涵上的异化。现代技术的社会属性在殖民地社会被放大了,他们不再仅仅是一个具有特定实用功能的工具,而是社会地位、性别关系、族群差异的标识物。缝纫机在印尼的推广也反映了资本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给殖民主义带来的活力以及对印尼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影响。
所著《自行车、港口与缝纫机:西方基建与日常技术在亚洲的相遇》,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在近代,西方殖民帝国和亚洲传统帝国,都在通过各种基建进行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强化对国家的治理。本书以奥斯曼帝国、英属印度、英属锡兰、荷属东印度、湄公河三角洲以及菲律宾等地区为个案,以这些地区的饮水工程、港口建设以及自行车、缝纫机、发动机、厨房的推广为线索,用生动的细节剖析了亚洲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展现了西方基建所带来的社会变迁和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巨大改变。
绝地反击!A股迎来大反攻,医药股史诗级暴涨,什么信号?此3000非彼3000,有何深意?这才是投资必需品
战地婚礼!乌政府军知名女狙击手在前线部门发文,对独居、空巢、失能等老年人要定期开展探访关爱
摊上事了!Jean Paul Gaultier被起诉侵权或面临高额罚款
相关文章
- 拼布缝纫创意作品大赛举行
- 深天马A(000050SZ):中航国际厦门拟将所持149%股份协议转让给中航国际实业
- 居然之家威海首家分店开业
- 静海农家女:“缝纫我在行为了防控疫情我得去”
- 小偷被抓!竟要求法院重判!只为在监狱学缝纫机技术!
- 缝纫机底线带不上来怎么办 缝纫机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 世界上最会用缝纫机的人别人缝衣服他用来绘画
- 老人街边修缝纫机:被骗2000
- 美自华进口缝纫机份额缩减
- 揭秘大阅兵上掠过的特殊材质五星红旗
- 神奇!每条窗帘都有专属二维码
- 踩完离合会发生什么这波机械动图让你看懂!
-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新展开幕探讨光影图像
- 快资讯-鹿财经锦州缝纫活
- NeurIPS 2022|中山大学HCP实验室在AIGC领域的新突破:有效表示多样化衣物的3D神经表示模型
- 增设缝纫专业培训 中布职教合作交流进入新阶段
- 宁波造“黑科技”实现自动化立体缝纫 机器人“裁缝” 赛过老师傅
- 全部导航外包缝纫
- 私藏!渝北缝纫机博物馆等待恋旧的你
- 他被誉为最聪明的裁缝靠一招年收入30亿连阿里都要向他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