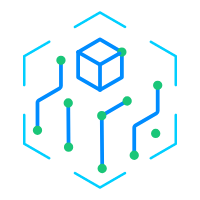散文|许钦明:大姨一家唱和谐(外四篇)
散文|许钦明:大姨一家唱和谐(外四篇)
散文|许钦明:大姨一家唱和谐(外四篇),吊装带缝纫机,缝纫线分线器,结实的缝纫线,
大姨家在冠县辛集乡岑庄村东北角,大门朝东,有着宽敞的三间堂屋和东西各三间的厢房。堂屋里住人,东屋里做饭,西屋是磨房,里面还堆放着一些杂物。宅院北面是小小的果园,有十多棵枣子、酸梨、杜梨和臭椿树。宅院东面是处场院和猪圈,场院东面靠猪圈的地方每年都种满了秫秸花。那花直立挺拔的杆子像棵棵高粱秸,枝叶间镶满单色或双色的红、黄、白、紫的花朵,争奇斗艳,煞是一道亮丽的乡下风景。
大姨高高胖胖的,黝黑的圆脸庞,粗哑的声音里透着亲切。我最爱去大姨家走亲戚,去了大姨就忙不跌地给我拿糖块和零食。姨家小四儿张保法和我同岁,但比我生月小点。我俩一块儿玩疯啦,带着他家的“四眼”(眼上面两撮黄毛就像两只眼)大黑狗,村前村后地乱窜。一会儿骑上他家园子里的歪脖子老梨树去夠梨,一会儿又去采那些秫秸花。一次,我俩大约六、七岁时,跑到村东南小河旁玩耍。看见一位白胡须飘胸的老者,坐在砖砌的排水沟沿上,眼前一群小孩子蹦蹦跳跳的。里面有两个浓眉大眼的双生女孩,脖子里都挂着用红头绳系着的两个李子。她们一跳,那紫红圆润的李子摇来摇去的,令人眼馋。老者看见我是来走亲戚的小孩,连忙从一个女孩脖颈上摘下一对李子,笑眯眯地送给我,我还真的就笑纳啦。
四弟消瘦的个头,圆圆脸细脖颈,说话哩哩啰啰的,是个老成孩子。他长相既不像大姨,也不像姨夫。我就问母亲,母亲说,你四弟是从黄河边上抱来的。你大姨生过孩子,都长得和小武官似的,可惜没成人,就托人抱了个来。小四儿在他老家弟兄五六个,按排行就叫小四儿。四弟尽管瘦弱,但在姨夫姨母的呵护下健康成长。当四弟弱冠之年成人后,姨父把他叫到跟前,说明了他的身世,让他回老家认爹娘。四弟回到黄河岸边的老家,见到了生身父母和几个哥哥,从此往来甚密。四弟感恩养父母,还是在岑庄扎下了根。
大姨姊妹七人,她是老大,有三弟三妹,我母亲是老小。大姨家离姥娘家大夫人寨不隔村,只有四里地。姊妹们的事大姨都帮姥娘操着心,照管这个照顾那个。当然最关照的还是我母亲,连我姑家盖房子还从大姨家拿了些土改拆楼余下的木板。母亲与大姨最亲近,我也去的次数最多。1959年春上,家里揭不开锅,村里的树叶大凡能吃的几乎都吃光啦,母亲让我去大姨家求助。我扒了两筐她家后院子里的臭椿树叶,大姨给煮熟用凉水浸泡后攥成团,又添了一些地瓜面的窝窝头儿,我揹着高兴地回了家。那臭椿叶虽说还是有点臭,但比杨树叶子吃起来好嚼好咽多啦。1961年春天,一个清冷的上午,在贾镇中学刚上完头节课,三姨家保元哥匆匆忙忙地跑去找我,说大姨去世啦。我赶忙请了假,跑去奔丧,在大姨灵前磕了四个头,大哭一场。大姨逝世那年,她才49岁,我记不起她得的什么病,听大人说大姨得病后吐血尿血,一病而逝。大姨属鼠的,生于1912年。
大姨夫张士敬,高高的个子一表人才,说话响亮而热诚。自打解放后,他就当村长,一直当到老。姥娘的四个女婿中,唯他是姥娘眼中的红人。姥娘逝世出殡时,大姨夫行三跪九叩礼,哭得鼻子一把泪一把的,在场的人均为之动情。我结婚前,大姨夫到我家住了几天,帮助收拾新房,用苇子编隔山。我结婚后,母亲告诉我:你大姨夫总挂着你,他来给你编隔山时,就得癌症啦,也没等到你从部队回来结婚,就走啦。为此,我对姨夫一直心怀愧疚。
大姨走后两年,姨夫迎来一位续大姨。续姨中等身材,方脸大眼睛,皮肤白皙,人利利落落的,说话清晰响亮,对亲戚格外亲热,和亲的大姨一样。续大姨会缝纫,带来一架上海牌的缝纫机。那时我在聊城一中念高中,看到有的同学穿西式裤子,羡慕得不得了。我和大姨说啦,从家里拿来母亲织的白、兰、紫三色人字呢粗布,大姨给我做了一条西式裤。我穿着那条裤子甚觉得意,一直到脱去学生装换上军装。大姨还手把手教会了大妹妹做帽子、剪裁缝制衣服、绣花,大妹妹又教会了四个小的妹妹,用这些手艺在生产队里工换工,到集上卖绣品挣钱,极大地改善了家庭经济窘境。
续姨从甘官屯乡梅庄改嫁而来,带着一个男孩子叫李乃良,属牛的,小我两岁。乃良瘦高挑儿的个,眉清目秀的像个奶油小生。初中毕业后就去山西某剧团找他的生父。他生父是该剧团团长,把他培养成了一个优秀小生。一次去大姨家,看到了他的戏妆照,他饰演一位小丑角色,被一个女人揪着耳朵,做十分痛苦状,让人觉得很搞笑。但我早已忘记他演的这是一出什么戏。听说,乃良找了一位剧团驻地附近农村的女孩做媳妇,为他生了两个男孩。可后来又另娶新欢,抛弃了原配的妻子。由此可见,有其父必有其子,乃良的父亲不是把儿子和原配妻子抛弃,又另找了个小媳妇吗!
四弟保法娶了本村一位姑娘为妻,把家庭经营得和美幸福。弟妹中等身材微胖,四方大脸的,勤勉厚道,生育两男两女。弟妹也是跟养父母---她的姨夫、姨母长大。后来四弟两口子为续姨、弟妹的老姨,两位都没有血缘的老人养老送终,尽心侍奉,传为美谈。
2011年深秋,一个阴霾的天气里,太阳有气无力地划过正午的天空,一位身体瘦弱的牧羊老人,在冷风里啃了几口干粮,顿觉身体不适,一个踉跄摔倒在河崖上。他得了急性脑溢血走啦,他离开了这个充满冷暖和诗意的世界。他伺候老的,拉巴小的,耗尽了全部心血。然而他,还没等到让儿女们伺候,就毅然决然的走啦,走的是那样步履匆匆。走时,他没躺在温暖的家里,没躺在医院的病房里,而是躺在冰凉的小河旁。身边没有亲人,守候他的是咩咩叫着的羊群,还有他那把无数次甩响的长鞭。秋风唱响哀乐,羊群呜咽流泪,残阳也目不忍睹地躲在了浮云身后。认出他的人告诉了我的嫁在赵庄的二妹,二妹又转告了同村四弟的大闺女,安排了他的后事。
四弟,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你究竟生在哪里,原本姓甚名谁,但我由衷地钦佩你:你,一株来自黄河边上的幼苗,在鲁西大地的岑庄,长成了一株茁壮的大树;我不知道你本来的血缘,可我明白你传承了张家的祖脉;你以赢弱的身躯担负了四位老人生老病死的重担,你养育了精明能干的后代。你,四弟,不是亲生胜似亲生,我要为你歌唱!
著名京剧《红灯记》里,有着一家三代本不是一家人,为革命高举红灯走到一起的革命故事,非常感人。再看大姨一家人:姨夫张姓,岑庄人;大姨任姓,大夫人寨人;续大姨从墨庄改嫁来岑庄,不知其姓;四弟领养来的,不知其原姓;乃良弟李姓,墨庄人;四弟媳李姓,迟庞庄人,投养母---亲姨来岑庄;四弟媳的姨妈,不知其姓。一家两代七口人六种血缘,先后都过得和和美美的,每个成员都有着不寻常的人生,共同把岑庄东北角这座农家小院,演绎成鲁西乡下一朵盛开的奇葩。
大妹妹许钦梅,乳名大女,属虎的,生于1950年,故于2004年,享年55岁。大妹和我是挨肩的,她下面还有四妹一弟。作为一个老少三代11口人的大家庭来说,我身为长子,应该早早承受家庭之重担。然而我没有,我一直读书,没做过农村社员或者农民。那么替我承受家庭之重担的,就自然落到大女妹妹和二妹妹身上。
荒年岁月的1960年,我考上了贾镇初中。迫于家境困难,家中老人讨论孩子们上学的事。我说,我不上学啦,让妹妹上。父亲不同意,说砸锅卖铁也得供你上,等你上学成功了,咱家就有了希望。你的两个妹妹就不能上学啦,都上学咱家供不起。这是父亲严肃的决定,也是全家人的共同意愿。
于是,上三年级的大妹和上一年级的二妹就辍学啦。尽管老师好几次去家里动员妹妹返校,但父亲还是不为所动。妹妹辍学后,整天下地挣工分,割草喂羊喂猪,种自留地,小小年纪就成了大家庭的顶梁柱。
1962年冬天,一天下午四点多钟的样子,我和同学正在贾镇南面桥上往学校走,忽听后面一个女孩叫哥哥,扭头一看正是大妹妹。她骑着家里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围着一条花格格的方围巾,看到我连忙从车子上下来。我说,你怎么来啦?她说我给你送干粮,这几个馍馍和枣卷子是上亲戚剩回来的,咱娘说你吃了一星期的地瓜啦,让你改改饭食呢,家里都没留一个。我说,你看天都快黑啦,你回去吧,路上骑慢点。大妹扭头骑上车子,慢慢消失在冷风中。
等到我高中毕业,正赶上,在学校闹腾了两年后,1968年我步入军营,两年后提了干。我有了一些收入,办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台青岛出的工农牌缝纫机。由战友从胶南捎到齐河农场,再由姨家表哥从那里骑自行车驮回老家。
这台缝纫机是我对妹妹的感恩,也是对妹妹最好的礼物。那时农村里时兴三大件,即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其中尤其缝纫机最难买,也最实用。大妹见到缝纫机如获至宝,很快跟大姨学会了缝制帽子,又跟人学会了绣花,跟妻子学会了做衣服。
大妹自学会缝纫活后,再没下过地,整天在家做衣服、绣花。白天忙一天,夜里还要点灯熬油地做活。队里人有找她做衣帽的,给她出工分,实行工换工。她的绣品主要是,儿童的兜肚、围脖和嫁娘的门帘腰之类,拿到周边集上去卖。有次给一家戏班子绣了几件戏服,就算大作啦。大妹很少赶集,赶集卖活主要是二妹的事。去赶的集主要是贾镇、辛集,连30多里地外的堂邑集也去。
我家人口多,挣得工分少,每年队上分配时,折算下来总欠队里的,大妹就拿攒的钱买工分。平时家里的零花钱也由她出,这样一来日子宽裕了些。再剩下些钱,大妹就自己准备嫁妆用。
1976年7月16日,是年27岁的大妹嫁给西张庄曹家一名复员军人,生3子。在29年的婚姻生活中,过得极度艰辛。拼着命侍弄那几亩薄地,尽心照顾好几个孩子,吃不好,穿不暖。一次与四妹抬着一袋子面,来我这里。一进门,只见她蓬头散发的样子,踏拉着一双旧塑料拖鞋,我和妻子都倍感心寒。妻子赶忙取出才买来的一双花布鞋,给她换上,还责怪她衣冠不整洁。我心想,她过得实在是难哪。
记得大妹最快乐的日子,就是没黑夜没白日地做缝纫活,裁、剪、绣,熨地忙个不停,累啦躺一会儿起来再做。每当我回家探亲,带来一提包减价的花布头,她总是抢过钥匙把那些东西翻出来。从压水井里压些水泡泡,拧干,挂满院中的铁丝绳。然后由她做主,给6个姊妹每人做一件新衣服。
大妹嫁人后,没听她讲述过有什么快乐的日子,有的只是困苦与辛酸。她不再添什么新衣服,也从不打扮。她像一头奶牛,为子女挤干了奶,还要下地拼命劳作。妻子心疼她,每年给她买件新衣服,把替换下来的衣服也送给她。
2004年初,以后的每个日子对她来说,都充满了阴霾。她得了癌症,从冠县医院转到聊城市医院。亲戚们凑钱给她做了手术,她操劳了一生,连治病的钱都没有。术后伤口迟迟不癒,她知道自己不行啦,很是悲伤。在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她给我来过一个电话:哥哥,你看我这怎么的呢,刀口还是没长好。她已没有活下去的希望,我只有劝她往好处想。
这年7月17日,她带着诸多的遗憾和无奈离开了这个世界。55岁的人生,怎么能算老呢?她辛劳短暂的一生,为娘家人和婆家人倾尽爱心,做出了无私奉献。你为什么要脚步匆匆地走呢?在娘家生活了26年,在婆家生活了29年,大家都喜欢你,时常挂念着你,你还没有来得及享受人生,怎么就走了呢。
今年7月17日,是你逝世27周年的忌日。我提前写下这篇祭文,纪念你,表达我永远的思念。我两天抒写完此文,哭了3次 ,以至最后嚎啕起来。
童年夭亡的胞弟小泉,一直活在我的心中。小泉是母亲的第四个孩子,属蛇的,生于1953年,逝于1958年。一个6虚岁的十分可爱的孩子,像是还没有来得及绽放的花骨朵,就早早地凋谢啦。
泉是8姊妹中长得最漂亮、最聪明的孩子。他平头正脸的,长弧脸,尖下巴,高鼻梁,大眼睛,双眼皮,身干柔韧协调,活泼好动,能说会道的小嘴,甚得家人喜爱。爷爷不止一次自豪地说,这可好,我们家几辈子单传,有了这俩孙子,以后就人烟兴旺啦。
可迟庞庄的姨爷爷李玉煌不认可我爷爷的说法,他警告说:你看,这俩孩子,一个老成厚道,一个泼辣刁钻,性格不合哦,以后还不知怎样里。当时我听了那话,心里好生气。心想,你这个烧砖窑的老头子瞎说什么呢!我最喜欢弟弟,弟弟也总爱和我玩,一出门就拽着我的手,生怕丢了他。可姨爷爷的一番话,竟成了箴言。
泉弟一岁多,我就上小学一年级啦。弟弟想找我玩,总让母亲领着他去下学的路口迎接我,见着我就张开臂膀让我抱。我抱不起来,只好两臂楼着他的腰,像拔罗卜似的从地上拔起来,轮几圈。弟弟总喜欢这样,喜得咯咯的。我总爱带着他摸蜘了猴,在沙土窝里翻喇叭虫。他拿着那个铁皮小罐子,见我逮住了,就伸着小手要过去塞进罐里,
泉弟小时候很淘的,大人也没功夫整天看着他,他就满村子找伙伴玩。他最爱找的就是小结实和小五子。小结实爱放纸飞机,斗蛐蛐,抓鱼,抓蛤蟆。小五子爱投杏核,把杏核钻眼灌了铅,沉甸甸的,一投一个掇窝。
一次放学后,奶奶急火火地说:二泉子把那个和面用的大广盆弄打啦,怕挨打,跑出去一下午也没回来。我说我知道他在哪里,放下书包,一溜小跑到了结实家。果不其然,他俩个正在摔胶泥,捏泥人呢。弟弟怯怯地说:我打了盆,奶奶说爹回来要打我,我不回去。我劝说着他爹不打你,连拉带拽地领他回了家。
1958年的夏天,弟弟发病啦。他只喊肚子痛,摸着他的肚子里面起疙瘩,身上发烧,有时痛得在地上打滚。那时缺医少药的,谁家也没钱,又能到那里看病呢。于是,我去西张庄姨家找药,是姨家东邻居二奶奶给找了一包打蛔虫的药。谁也不知道弟弟是啥病,就认为他肚子里有蛔虫,便灌了药下去。你说也算管事,第二天弟弟便开始拉虫子,拉了一根又一根,有的几根虫子缠成团。弟弟在院子里艰难地挪动着身子,拉了有十几根虫子,我一根根除到茅坑里。
打那以后弟弟显得好些啦,我们一家人也稍稍松了些心。可是,不久弟弟的病又越发严重。发烧不退,开始发喘,嘴唇干得起了皮,吃不下东西。西张庄三姨夫还给他买来蜂蜜和一瓶葡萄糖粉,一勺勺地喂。
转眼到了初冬,弟弟似乎也感觉着他不行啦,对同村的姑父说:你们救救我吧,我长大了给你挑水,孝顺你。姑父让人给出河工的父亲捎信儿,赶回来,两个人轮流背着小泉,走了70多里地,来到聊城地区医院看病。医生还没诊断完,躺在诊床上的弟弟就再也没醒过来。医生要求留下遗体做解剖用,可父亲没有答应。两人背着小泉往回走,天黑下来,两人又饿又累,走不动啦,只好到离城不远的公路旁边一个村子里借了把铁锨,在土岗的冻土上挖个坑,把弟弟埋啦。
弟弟夭亡后,一家人都倍感凄凉。我心里闷闷的,少了兄弟的亲情与快乐。打那以后,谁也不再提小泉,他成了一家人的伤心地儿。
1963年,我考入了聊城一中这所有名的中学。本来上三年的高中就可以考大学啦,可没想到文革把我们这些莘莘学子拌了一脚,在校闹革命又是两年。5年里,我沿着济邯公路来回走了1万5千里。天冷白天走,天热夜里行。每每路过聊城西关外公路旁边那个村子,我就想起弟弟小泉。在那个寒冷的夜晚,弟弟被埋啦。他会不会又复活,穿着我那件过三生时姨妈给做的的绿地碎花的棉袍子,走到一户农家,被收留后长大成人了呢?尽管我知道这不会是真的,但我仍然常常这样地遐想。
1968年春天,我步入军营。13年后我调回聊城军分区,5年后,我转业到地方,就住在火车站附近。这里,也许正是我朝思梦萦的掩埋弟弟的场所吧?当年,从市医院向西走济邯公路,现在的火车站和汽车西站是必经之地。火车站近郊的村子老柳头村西,原先就有一些沙土岗子。弟弟,你被埋在哪里?你就被埋在那个沙土岗子,现在的那个火车隆隆驰过的铁道旁边吗?当我上街或者散步时,我总是若有所思,弟弟的音容笑貌,弟弟小时候的影子,像旋风一般追逐着我。
我永远猜不着弟弟到底埋在那里,因为老人家并没有告诉我具体地点,当时他们也记不住哪里是哪里。我也没有多问,我没法问或者不敢问,这是一家人的伤疤呀。假如人有灵魂,但愿弟弟的灵魂追随着我,给我永远的思念,夜里时时潜入我的梦境,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天真烂熳的岁月。
母亲姐妹四人,她是老小。二姨最苦命却最长寿,她生于1917年,逝于2021年2月7日,享年104岁。我每年都去看望她,姨临终耳不聋,眼不花,面色滋润不显衰老,说起话来思路也很清晰。只是有年头腿脚不好,长期卧床,满头白发。
二姨早年嫁到丁寨乡黄寨子,姨夫是个孤儿。姨夫父母早丧,跟着院中一位叔伯生活。结婚时正值日伪时期,姨夫住着两间茅草房。屋里一盘土炕,除去吃饭的家什,里面空荡荡的。从结婚开始,两人就过起了十分困窘的日子。
一九四三年,鲁西北闹饥荒,村中人外出讨饭,十室九空。姨守在家里待产,秋后生下一个男婴。家里没啥吃的,姨夫连忙去野地里找到几个苦瓜,拿来家煮了给姨吃,算是坐月子的”营养餐”。姨和姨夫说:你看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咱给孩子起个啥名子呢?我看就叫“小乱”吧。姨夫说也是哦,咱就盼着孩子平安长大,再不过这兵荒马乱挨饿的日子。后来姨又生了四个儿子,日子依然过得很艰难。
一九六三年夏,我去聊城一中读高中,三年高中读了五年(其中两年文革)。七十里地的路我没坐过一次公共汽车,那时上得起学就很难啦,哪有闲钱买车票啊。半月回一次家,靠着个人的“11路”来回穿梭在聊邯公路上,五年累计走了一万五千里。
回家时,和同学作伴从星期五晚饭后走一夜,星期六早晨八九点钟到家。回校时,星期天下午走24里地先住到姨家。姨家是上学路上必经之地,到学校还有四十多里地。为了节省体力,减轻疲劳,姨家便成了我上学路上的驿站。
那时姨家在村北有了一座砖基的泥土房,连大门和围墙也没有。三间正房,东间是土炕和灶台,中间是条桌和一张床,西间喂着一头牛。我星期天傍黑到了姨家住下,第二天摸黑起来上学去。姨让我睡床上,怕我冷拿来姨夫到内蒙打工带回的毛毯盖上。我走时,姨都是天不亮就早早起来给我熬粥、热干粮,让我吃得热热乎乎的路上不冷。
乱哥大名徐以惠,自小聪慧,因家里穷、兄弟多,只念了个小学。辍学后自学成才,写一手好字,绘画也有造诣。我念高中时,乱哥和我交流书法,我是自叹弗如。乱哥年轻时就在村里当会计,帐码钱款理得清清楚楚。乱哥的会计水平名声在外,以至于邻村和供销社也请他记账理财。
乱哥在六十年代艰困时期,娶了一位外地瘦弱女子为妻,育有一男两女。乱哥忠厚老成,帮助亲戚尽力而为。我家翻盖房屋,乱哥半夜起身,夜走二十多里地到我家帮忙,晚饭后再走回去。乱哥上孝父母,下爱兄弟,勤俭顾家。乱哥五十多岁时,积劳成疾,一病而逝。
三姨家是冠县兰沃乡西张庄,离我们村四里地,那是好大一家子人。在村西头一个深胡洞里,大门朝东,两座并排各三间的堂屋,三间东屋是厨房。东堂屋爷爷奶奶住,姨和孩子们住西堂屋。姨年轻时上有公公婆婆,还有一位祖奶奶,下有小姑子和小叔子,再加上姨夫和他们的五个女,一家十二口人,光是一天烧三顿饭就够她忙乎的。
1959年秋天,我从贾镇完小转学到西张庄完小上六年级。每天天不亮就去上学,中午带一顿干粮,下午放学回家。姨看我上学路上冷,风里雨里地遭罪,中午也吃不上热饭,就让我住在她家里。这样,家里又多了一张嘴,给姨添累。姨让我睡在西堂屋东间一张床上,铺好被褥,又拿来从未盖过的新被子压风。我睡得暖暖和和的,比赵店村那所食宿学校住的简直天壤之别。
那年月,是乡下最困难的日子,家家以地瓜为主粮。每半月我回家带来一箢子地瓜面,算是我的口粮。姨总是把我那带苦味的地瓜面与玉米面掺和在一起,做成二和面的窝窝头或者锅饼,大家吃一样的饭。
老奶奶有四个儿子,轮流在各家吃饭。我头一次见她:中等身材 ,微胖,背有些驼,一头白发,黝红的脸膛,嘴角总是挂着笑意。我按照母亲嘱咐的先问安好:“老奶奶您旺祥不?”老奶奶高兴地哈哈大笑:“我啊,旺祥着哩”!说着,把我搂到怀里,抚摸着我的额头,让人感到是那样的亲近。
每逢放了学,我就打扫院子,拾鸡粪,干些眼色活,一家人都夸我懂事、勤快。老奶奶总是不让这些,说:“小来,快坐奶奶这里歇歇”。天冷的时候,她用那温暖的起了皱褶的双手攥紧我的手:“看看,这小手都冻红了吧!”每当吃饭时,老奶奶总是说:“小来,你拿好面干粮吃,别见外。”当我抢先拿了剩窝窝,奶奶急地下命令,让四姑给我换成新的吃。
爷爷仪表堂堂,须髯飘胸,声若洪钟,好像小时候看过三国演义里的某个人物。爷爷经常夸我学习好,还当班里的学习委员。刚过完春节,堂屋桌子上的主匣子还没移走,爷爷突然指着问我:“你看这祖宗牌位上的字,那个写的好哇?”我仔细端详了好一会儿,也没闹清哪个写得好,只好硬着头皮说:“这个旧些的牌位上的字写得好吧”。爷爷微微一笑:“这老牌位是咱村的私塾先生点的主,可那新点的牌位是请恁们村少拔贡点题的。”哦,我们村院中的名人---清末父子二拔贡---可是远近闻名啊。这不经意间,爷爷给我上了一课。
续奶奶年轻好多,白白胖胖的,但是个盲人。除我姨夫是头前的孩子外,奶奶又生了四姑和白叔。奶奶平日里洗洗衣服,帮姨做饭烧火。奶奶整日里乐呵呵的,待人亲切和蔼。奶奶对姨没啥长辈的架子,两人和和美美像母女。
姨夫建国后就早早参加了工作,初在贾镇供销社当经理,后又改任镇政府民政助理,一直到退休。姨夫高高的个头,瘦瘦的,声音低沉而温和,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姨夫带供销社的人轮流下村送货,到我村时给我买的苹果,是第一次尝鲜呢,至今回味悠长。一九五七年,姨夫下乡整顿农业社,住我家东屋里。每次都是我把饭送过去,吃完我把碗筷收回来。上世纪七十年代,家里点灯、烧饭缺煤油,是我找姨夫想法买,救了燃眉之急。我家属随军时迁户口,姨夫骑自行车到县民政局办好手续,给我邮到部队,了却我一件心事。
老白叔比我大一岁,可上学比我晚一年。白叔小名老白,长得像奶奶,白白净净的。放了学,我俩一块去放羊,拾柴火。白叔对我很照顾,拾的柴火他背着,让我跟着就行。白叔娶了我高小同班同学韩路人王桂玲为妻,哈,女同学成了我婶子。他们育有一子一女,一家人过得很幸福。白叔在村里当了多年的红白理事会执事,为村里人操持婚丧嫁娶的事,很是受人敬重。
四姑高高胖胖的,仿爷爷的身材,比白叔还高半头。她地里的活很能干,家里的事也能操持,与姨处得很和谐。四姑小学毕业后务农,后来嫁到了李辛村,姑父姓李,在贾镇医院当医生,也是我高小的同学。你看,这同学又成我姑父啦!真是应了古人那句话:人生何处不相逢。四姑在李辛村当赤脚医生,为乡亲们看病拿药,接新生儿,深受全村人敬重。
保元哥和四姑同岁,比白叔还大两岁呢。我念高小时,他就在贾镇读中学,中学毕业后回家务农。爷爷看他不像干活的料,常教训他。一年的冬天挨了吵,跑到我家,不想回去。好说歹说地劝他,直到半夜我才送他回到家。改革开放后,他赶集卖布卖衣服。我在聊城军分区时,他还来军分区家属工厂进过两次腈纶内衣。后来他又在家养鸡,在一次去县城进鸡饲料时,不幸从公共汽车上摔下来,不治身亡。当时汽车门没有关,汽车便急速行驶,元哥被甩下车摔伤头部致死,汽车未停驶离。姨夫来聊城找我处理此事,我找到汽运公司的同学老刘,查明该车属于邯郸汽运公司及其车号,确定为行车事故并予以赔偿。
西张庄完小,西张庄姨家,我从小喜欢的地方,我永远怀念的地方,我想你们啦!
【作者简介】许钦明,山东冠县人。从小,农村儿童。读书,聊城一中。考大学,遇见。从军18载,军职正营。聊城烟草13年,干的中层。老来寻觅文苑趣,撒播花草慰心灵。
大姨家在冠县辛集乡岑庄村东北角,大门朝东,有着宽敞的三间堂屋和东西各三间的厢房。堂屋里住人,东屋里做饭,西屋是磨房,里面还堆放着一些杂物。宅院北面是小小的果园,有十多棵枣子、酸梨、杜梨和臭椿树。宅院东面是处场院和猪圈,场院东面靠猪圈的地方每年都种满了秫秸花。那花直立挺拔的杆子像棵棵高粱秸,枝叶间镶满单色或双色的红、黄、白、紫的花朵,争奇斗艳,煞是一道亮丽的乡下风景。大姨高高胖胖的,黝黑的圆脸庞,粗哑的声音里透着亲切。我最爱去大姨家走亲戚,去了大姨就忙不跌地给我拿糖块和零食。姨家小四儿张保法和我同岁,但比我生月小点。我俩一块儿玩疯啦,带着他家的“四眼”(眼上面两撮黄毛就像两只眼)大黑狗,村前村后地乱窜。一会儿骑上他家园子里的歪脖子老梨树去夠梨,一会儿又去采那些秫秸花。一次,我俩大约六、七岁时,跑到村东南小河旁玩耍。看见一位白胡须飘胸的老者,坐在砖砌的排水沟沿上,眼前一群小孩子蹦蹦跳跳的。里面有两个浓眉大眼的双生女孩,脖子里都挂着用红头绳系着的两个李子。她们一跳,那紫红圆润的李子摇来摇去的,令人眼馋。老者看见我是来走亲戚的小孩,连忙从一个女孩脖颈上摘下一对李子,笑眯眯地送给我,我还真的就笑纳啦。
四弟消瘦的个头,圆圆脸细脖颈,说话哩哩啰啰的,是个老成孩子。他长相既不像大姨,也不像姨夫。我就问母亲,母亲说,你四弟是从黄河边上抱来的。你大姨生过孩子,都长得和小武官似的,可惜没成人,就托人抱了个来。小四儿在他老家弟兄五六个,按排行就叫小四儿。四弟尽管瘦弱,但在姨夫姨母的呵护下健康成长。当四弟弱冠之年成人后,姨父把他叫到跟前,说明了他的身世,让他回老家认爹娘。四弟回到黄河岸边的老家,见到了生身父母和几个哥哥,从此往来甚密。四弟感恩养父母,还是在岑庄扎下了根。
大姨姊妹七人,她是老大,有三弟三妹,我母亲是老小。大姨家离姥娘家大夫人寨不隔村,只有四里地。姊妹们的事大姨都帮姥娘操着心,照管这个照顾那个。当然最关照的还是我母亲,连我姑家盖房子还从大姨家拿了些土改拆楼余下的木板。母亲与大姨最亲近,我也去的次数最多。1959年春上,家里揭不开锅,村里的树叶大凡能吃的几乎都吃光啦,母亲让我去大姨家求助。我扒了两筐她家后院子里的臭椿树叶,大姨给煮熟用凉水浸泡后攥成团,又添了一些地瓜面的窝窝头儿,我揹着高兴地回了家。那臭椿叶虽说还是有点臭,但比杨树叶子吃起来好嚼好咽多啦。1961年春天,一个清冷的上午,在贾镇中学刚上完头节课,三姨家保元哥匆匆忙忙地跑去找我,说大姨去世啦。我赶忙请了假,跑去奔丧,在大姨灵前磕了四个头,大哭一场。大姨逝世那年,她才49岁,我记不起她得的什么病,听大人说大姨得病后吐血尿血,一病而逝。大姨属鼠的,生于1912年。
大姨夫张士敬,高高的个子一表人才,说话响亮而热诚。自打解放后,他就当村长,一直当到老。姥娘的四个女婿中,唯他是姥娘眼中的红人。姥娘逝世出殡时,大姨夫行三跪九叩礼,哭得鼻子一把泪一把的,在场的人均为之动情。我结婚前,大姨夫到我家住了几天,帮助收拾新房,用苇子编隔山。我结婚后,母亲告诉我:你大姨夫总挂着你,他来给你编隔山时,就得癌症啦,也没等到你从部队回来结婚,就走啦。为此,我对姨夫一直心怀愧疚。
大姨走后两年,姨夫迎来一位续大姨。续姨中等身材,方脸大眼睛,皮肤白皙,人利利落落的,说话清晰响亮,对亲戚格外亲热,和亲的大姨一样。续大姨会缝纫,带来一架上海牌的缝纫机。那时我在聊城一中念高中,看到有的同学穿西式裤子,羡慕得不得了。我和大姨说啦,从家里拿来母亲织的白、兰、紫三色人字呢粗布,大姨给我做了一条西式裤。我穿着那条裤子甚觉得意,一直到脱去学生装换上军装。大姨还手把手教会了大妹妹做帽子、剪裁缝制衣服、绣花,大妹妹又教会了四个小的妹妹,用这些手艺在生产队里工换工,到集上卖绣品挣钱,极大地改善了家庭经济窘境。
续姨从甘官屯乡梅庄改嫁而来,带着一个男孩子叫李乃良,属牛的,小我两岁。乃良瘦高挑儿的个,眉清目秀的像个奶油小生。初中毕业后就去山西某剧团找他的生父。他生父是该剧团团长,把他培养成了一个优秀小生。一次去大姨家,看到了他的戏妆照,他饰演一位小丑角色,被一个女人揪着耳朵,做十分痛苦状,让人觉得很搞笑。但我早已忘记他演的这是一出什么戏。听说,乃良找了一位剧团驻地附近农村的女孩做媳妇,为他生了两个男孩。可后来又另娶新欢,抛弃了原配的妻子。由此可见,有其父必有其子,乃良的父亲不是把儿子和原配妻子抛弃,又另找了个小媳妇吗!
四弟保法娶了本村一位姑娘为妻,把家庭经营得和美幸福。弟妹中等身材微胖,四方大脸的,勤勉厚道,生育两男两女。弟妹也是跟养父母---她的姨夫、姨母长大。后来四弟两口子为续姨、弟妹的老姨,两位都没有血缘的老人养老送终,尽心侍奉,传为美谈。
2011年深秋,一个阴霾的天气里,太阳有气无力地划过正午的天空,一位身体瘦弱的牧羊老人,在冷风里啃了几口干粮,顿觉身体不适,一个踉跄摔倒在河崖上。他得了急性脑溢血走啦,他离开了这个充满冷暖和诗意的世界。他伺候老的,拉巴小的,耗尽了全部心血。然而他,还没等到让儿女们伺候,就毅然决然的走啦,走的是那样步履匆匆。走时,他没躺在温暖的家里,没躺在医院的病房里,而是躺在冰凉的小河旁。身边没有亲人,守候他的是咩咩叫着的羊群,还有他那把无数次甩响的长鞭。秋风唱响哀乐,羊群呜咽流泪,残阳也目不忍睹地躲在了浮云身后。认出他的人告诉了我的嫁在赵庄的二妹,二妹又转告了同村四弟的大闺女,安排了他的后事。
四弟,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你究竟生在哪里,原本姓甚名谁,但我由衷地钦佩你:你,一株来自黄河边上的幼苗,在鲁西大地的岑庄,长成了一株茁壮的大树;我不知道你本来的血缘,可我明白你传承了张家的祖脉;你以赢弱的身躯担负了四位老人生老病死的重担,你养育了精明能干的后代。你,四弟,不是亲生胜似亲生,我要为你歌唱!
著名京剧《红灯记》里,有着一家三代本不是一家人,为革命高举红灯走到一起的革命故事,非常感人。再看大姨一家人:姨夫张姓,岑庄人;大姨任姓,大夫人寨人;续大姨从墨庄改嫁来岑庄,不知其姓;四弟领养来的,不知其原姓;乃良弟李姓,墨庄人;四弟媳李姓,迟庞庄人,投养母---亲姨来岑庄;四弟媳的姨妈,不知其姓。一家两代七口人六种血缘,先后都过得和和美美的,每个成员都有着不寻常的人生,共同把岑庄东北角这座农家小院,演绎成鲁西乡下一朵盛开的奇葩。
大妹妹许钦梅,乳名大女,属虎的,生于1950年,故于2004年,享年55岁。大妹和我是挨肩的,她下面还有四妹一弟。作为一个老少三代11口人的大家庭来说,我身为长子,应该早早承受家庭之重担。然而我没有,我一直读书,没做过农村社员或者农民。那么替我承受家庭之重担的,就自然落到大女妹妹和二妹妹身上。
荒年岁月的1960年,我考上了贾镇初中。迫于家境困难,家中老人讨论孩子们上学的事。我说,我不上学啦,让妹妹上。父亲不同意,说砸锅卖铁也得供你上,等你上学成功了,咱家就有了希望。你的两个妹妹就不能上学啦,都上学咱家供不起。这是父亲严肃的决定,也是全家人的共同意愿。
于是,上三年级的大妹和上一年级的二妹就辍学啦。尽管老师好几次去家里动员妹妹返校,但父亲还是不为所动。妹妹辍学后,整天下地挣工分,割草喂羊喂猪,种自留地,小小年纪就成了大家庭的顶梁柱。
1962年冬天,一天下午四点多钟的样子,我和同学正在贾镇南面桥上往学校走,忽听后面一个女孩叫哥哥,扭头一看正是大妹妹。她骑着家里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围着一条花格格的方围巾,看到我连忙从车子上下来。我说,你怎么来啦?她说我给你送干粮,这几个馍馍和枣卷子是上亲戚剩回来的,咱娘说你吃了一星期的地瓜啦,让你改改饭食呢,家里都没留一个。我说,你看天都快黑啦,你回去吧,路上骑慢点。大妹扭头骑上车子,慢慢消失在冷风中。
等到我高中毕业,正赶上,在学校闹腾了两年后,1968年我步入军营,两年后提了干。我有了一些收入,办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台青岛出的工农牌缝纫机。由战友从胶南捎到齐河农场,再由姨家表哥从那里骑自行车驮回老家。
这台缝纫机是我对妹妹的感恩,也是对妹妹最好的礼物。那时农村里时兴三大件,即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其中尤其缝纫机最难买,也最实用。大妹见到缝纫机如获至宝,很快跟大姨学会了缝制帽子,又跟人学会了绣花,跟妻子学会了做衣服。
大妹自学会缝纫活后,再没下过地,整天在家做衣服、绣花。白天忙一天,夜里还要点灯熬油地做活。队里人有找她做衣帽的,给她出工分,实行工换工。她的绣品主要是,儿童的兜肚、围脖和嫁娘的门帘腰之类,拿到周边集上去卖。有次给一家戏班子绣了几件戏服,就算大作啦。大妹很少赶集,赶集卖活主要是二妹的事。去赶的集主要是贾镇、辛集,连30多里地外的堂邑集也去。
我家人口多,挣得工分少,每年队上分配时,折算下来总欠队里的,大妹就拿攒的钱买工分。平时家里的零花钱也由她出,这样一来日子宽裕了些。再剩下些钱,大妹就自己准备嫁妆用。
1976年7月16日,是年27岁的大妹嫁给西张庄曹家一名复员军人,生3子。在29年的婚姻生活中,过得极度艰辛。拼着命侍弄那几亩薄地,尽心照顾好几个孩子,吃不好,穿不暖。一次与四妹抬着一袋子面,来我这里。一进门,只见她蓬头散发的样子,踏拉着一双旧塑料拖鞋,我和妻子都倍感心寒。妻子赶忙取出才买来的一双花布鞋,给她换上,还责怪她衣冠不整洁。我心想,她过得实在是难哪。
记得大妹最快乐的日子,就是没黑夜没白日地做缝纫活,裁、剪、绣,熨地忙个不停,累啦躺一会儿起来再做。每当我回家探亲,带来一提包减价的花布头,她总是抢过钥匙把那些东西翻出来。从压水井里压些水泡泡,拧干,挂满院中的铁丝绳。然后由她做主,给6个姊妹每人做一件新衣服。
大妹嫁人后,没听她讲述过有什么快乐的日子,有的只是困苦与辛酸。她不再添什么新衣服,也从不打扮。她像一头奶牛,为子女挤干了奶,还要下地拼命劳作。妻子心疼她,每年给她买件新衣服,把替换下来的衣服也送给她。
2004年初,以后的每个日子对她来说,都充满了阴霾。她得了癌症,从冠县医院转到聊城市医院。亲戚们凑钱给她做了手术,她操劳了一生,连治病的钱都没有。术后伤口迟迟不癒,她知道自己不行啦,很是悲伤。在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她给我来过一个电话:哥哥,你看我这怎么的呢,刀口还是没长好。她已没有活下去的希望,我只有劝她往好处想。
这年7月17日,她带着诸多的遗憾和无奈离开了这个世界。55岁的人生,怎么能算老呢?她辛劳短暂的一生,为娘家人和婆家人倾尽爱心,做出了无私奉献。你为什么要脚步匆匆地走呢?在娘家生活了26年,在婆家生活了29年,大家都喜欢你,时常挂念着你,你还没有来得及享受人生,怎么就走了呢。
今年7月17日,是你逝世27周年的忌日。我提前写下这篇祭文,纪念你,表达我永远的思念。我两天抒写完此文,哭了3次 ,以至最后嚎啕起来。
童年夭亡的胞弟小泉,一直活在我的心中。小泉是母亲的第四个孩子,属蛇的,生于1953年,逝于1958年。一个6虚岁的十分可爱的孩子,像是还没有来得及绽放的花骨朵,就早早地凋谢啦。
泉是8姊妹中长得最漂亮、最聪明的孩子。他平头正脸的,长弧脸,尖下巴,高鼻梁,大眼睛,双眼皮,身干柔韧协调,活泼好动,能说会道的小嘴,甚得家人喜爱。爷爷不止一次自豪地说,这可好,我们家几辈子单传,有了这俩孙子,以后就人烟兴旺啦。
可迟庞庄的姨爷爷李玉煌不认可我爷爷的说法,他警告说:你看,这俩孩子,一个老成厚道,一个泼辣刁钻,性格不合哦,以后还不知怎样里。当时我听了那话,心里好生气。心想,你这个烧砖窑的老头子瞎说什么呢!我最喜欢弟弟,弟弟也总爱和我玩,一出门就拽着我的手,生怕丢了他。可姨爷爷的一番话,竟成了箴言。
泉弟一岁多,我就上小学一年级啦。弟弟想找我玩,总让母亲领着他去下学的路口迎接我,见着我就张开臂膀让我抱。我抱不起来,只好两臂楼着他的腰,像拔罗卜似的从地上拔起来,轮几圈。弟弟总喜欢这样,喜得咯咯的。我总爱带着他摸蜘了猴,在沙土窝里翻喇叭虫。他拿着那个铁皮小罐子,见我逮住了,就伸着小手要过去塞进罐里,
泉弟小时候很淘的,大人也没功夫整天看着他,他就满村子找伙伴玩。他最爱找的就是小结实和小五子。小结实爱放纸飞机,斗蛐蛐,抓鱼,抓蛤蟆。小五子爱投杏核,把杏核钻眼灌了铅,沉甸甸的,一投一个掇窝。
一次放学后,奶奶急火火地说:二泉子把那个和面用的大广盆弄打啦,怕挨打,跑出去一下午也没回来。我说我知道他在哪里,放下书包,一溜小跑到了结实家。果不其然,他俩个正在摔胶泥,捏泥人呢。弟弟怯怯地说:我打了盆,奶奶说爹回来要打我,我不回去。我劝说着他爹不打你,连拉带拽地领他回了家。
1958年的夏天,弟弟发病啦。他只喊肚子痛,摸着他的肚子里面起疙瘩,身上发烧,有时痛得在地上打滚。那时缺医少药的,谁家也没钱,又能到那里看病呢。于是,我去西张庄姨家找药,是姨家东邻居二奶奶给找了一包打蛔虫的药。谁也不知道弟弟是啥病,就认为他肚子里有蛔虫,便灌了药下去。你说也算管事,第二天弟弟便开始拉虫子,拉了一根又一根,有的几根虫子缠成团。弟弟在院子里艰难地挪动着身子,拉了有十几根虫子,我一根根除到茅坑里。
打那以后弟弟显得好些啦,我们一家人也稍稍松了些心。可是,不久弟弟的病又越发严重。发烧不退,开始发喘,嘴唇干得起了皮,吃不下东西。西张庄三姨夫还给他买来蜂蜜和一瓶葡萄糖粉,一勺勺地喂。
转眼到了初冬,弟弟似乎也感觉着他不行啦,对同村的姑父说:你们救救我吧,我长大了给你挑水,孝顺你。姑父让人给出河工的父亲捎信儿,赶回来,两个人轮流背着小泉,走了70多里地,来到聊城地区医院看病。医生还没诊断完,躺在诊床上的弟弟就再也没醒过来。医生要求留下遗体做解剖用,可父亲没有答应。两人背着小泉往回走,天黑下来,两人又饿又累,走不动啦,只好到离城不远的公路旁边一个村子里借了把铁锨,在土岗的冻土上挖个坑,把弟弟埋啦。
弟弟夭亡后,一家人都倍感凄凉。我心里闷闷的,少了兄弟的亲情与快乐。打那以后,谁也不再提小泉,他成了一家人的伤心地儿。
1963年,我考入了聊城一中这所有名的中学。本来上三年的高中就可以考大学啦,可没想到文革把我们这些莘莘学子拌了一脚,在校闹革命又是两年。5年里,我沿着济邯公路来回走了1万5千里。天冷白天走,天热夜里行。每每路过聊城西关外公路旁边那个村子,我就想起弟弟小泉。在那个寒冷的夜晚,弟弟被埋啦。他会不会又复活,穿着我那件过三生时姨妈给做的的绿地碎花的棉袍子,走到一户农家,被收留后长大成人了呢?尽管我知道这不会是真的,但我仍然常常这样地遐想。
1968年春天,我步入军营。13年后我调回聊城军分区,5年后,我转业到地方,就住在火车站附近。这里,也许正是我朝思梦萦的掩埋弟弟的场所吧?当年,从市医院向西走济邯公路,现在的火车站和汽车西站是必经之地。火车站近郊的村子老柳头村西,原先就有一些沙土岗子。弟弟,你被埋在哪里?你就被埋在那个沙土岗子,现在的那个火车隆隆驰过的铁道旁边吗?当我上街或者散步时,我总是若有所思,弟弟的音容笑貌,弟弟小时候的影子,像旋风一般追逐着我。
我永远猜不着弟弟到底埋在那里,因为老人家并没有告诉我具体地点,当时他们也记不住哪里是哪里。我也没有多问,我没法问或者不敢问,这是一家人的伤疤呀。假如人有灵魂,但愿弟弟的灵魂追随着我,给我永远的思念,夜里时时潜入我的梦境,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天真烂熳的岁月。
母亲姐妹四人,她是老小。二姨最苦命却最长寿,她生于1917年,逝于2021年2月7日,享年104岁。我每年都去看望她,姨临终耳不聋,眼不花,面色滋润不显衰老,说起话来思路也很清晰。只是有年头腿脚不好,长期卧床,满头白发。
二姨早年嫁到丁寨乡黄寨子,姨夫是个孤儿。姨夫父母早丧,跟着院中一位叔伯生活。结婚时正值日伪时期,姨夫住着两间茅草房。屋里一盘土炕,除去吃饭的家什,里面空荡荡的。从结婚开始,两人就过起了十分困窘的日子。
一九四三年,鲁西北闹饥荒,村中人外出讨饭,十室九空。姨守在家里待产,秋后生下一个男婴。家里没啥吃的,姨夫连忙去野地里找到几个苦瓜,拿来家煮了给姨吃,算是坐月子的”营养餐”。姨和姨夫说:你看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咱给孩子起个啥名子呢?我看就叫“小乱”吧。姨夫说也是哦,咱就盼着孩子平安长大,再不过这兵荒马乱挨饿的日子。后来姨又生了四个儿子,日子依然过得很艰难。
一九六三年夏,我去聊城一中读高中,三年高中读了五年(其中两年文革)。七十里地的路我没坐过一次公共汽车,那时上得起学就很难啦,哪有闲钱买车票啊。半月回一次家,靠着个人的“11路”来回穿梭在聊邯公路上,五年累计走了一万五千里。
回家时,和同学作伴从星期五晚饭后走一夜,星期六早晨八九点钟到家。回校时,星期天下午走24里地先住到姨家。姨家是上学路上必经之地,到学校还有四十多里地。为了节省体力,减轻疲劳,姨家便成了我上学路上的驿站。
那时姨家在村北有了一座砖基的泥土房,连大门和围墙也没有。三间正房,东间是土炕和灶台,中间是条桌和一张床,西间喂着一头牛。我星期天傍黑到了姨家住下,第二天摸黑起来上学去。姨让我睡床上,怕我冷拿来姨夫到内蒙打工带回的毛毯盖上。我走时,姨都是天不亮就早早起来给我熬粥、热干粮,让我吃得热热乎乎的路上不冷。
乱哥大名徐以惠,自小聪慧,因家里穷、兄弟多,只念了个小学。辍学后自学成才,写一手好字,绘画也有造诣。我念高中时,乱哥和我交流书法,我是自叹弗如。乱哥年轻时就在村里当会计,帐码钱款理得清清楚楚。乱哥的会计水平名声在外,以至于邻村和供销社也请他记账理财。
乱哥在六十年代艰困时期,娶了一位外地瘦弱女子为妻,育有一男两女。乱哥忠厚老成,帮助亲戚尽力而为。我家翻盖房屋,乱哥半夜起身,夜走二十多里地到我家帮忙,晚饭后再走回去。乱哥上孝父母,下爱兄弟,勤俭顾家。乱哥五十多岁时,积劳成疾,一病而逝。
三姨家是冠县兰沃乡西张庄,离我们村四里地,那是好大一家子人。在村西头一个深胡洞里,大门朝东,两座并排各三间的堂屋,三间东屋是厨房。东堂屋爷爷奶奶住,姨和孩子们住西堂屋。姨年轻时上有公公婆婆,还有一位祖奶奶,下有小姑子和小叔子,再加上姨夫和他们的五个女,一家十二口人,光是一天烧三顿饭就够她忙乎的。
1959年秋天,我从贾镇完小转学到西张庄完小上六年级。每天天不亮就去上学,中午带一顿干粮,下午放学回家。姨看我上学路上冷,风里雨里地遭罪,中午也吃不上热饭,就让我住在她家里。这样,家里又多了一张嘴,给姨添累。姨让我睡在西堂屋东间一张床上,铺好被褥,又拿来从未盖过的新被子压风。我睡得暖暖和和的,比赵店村那所食宿学校住的简直天壤之别。
那年月,是乡下最困难的日子,家家以地瓜为主粮。每半月我回家带来一箢子地瓜面,算是我的口粮。姨总是把我那带苦味的地瓜面与玉米面掺和在一起,做成二和面的窝窝头或者锅饼,大家吃一样的饭。
老奶奶有四个儿子,轮流在各家吃饭。我头一次见她:中等身材 ,微胖,背有些驼,一头白发,黝红的脸膛,嘴角总是挂着笑意。我按照母亲嘱咐的先问安好:“老奶奶您旺祥不?”老奶奶高兴地哈哈大笑:“我啊,旺祥着哩”!说着,把我搂到怀里,抚摸着我的额头,让人感到是那样的亲近。
每逢放了学,我就打扫院子,拾鸡粪,干些眼色活,一家人都夸我懂事、勤快。老奶奶总是不让这些,说:“小来,快坐奶奶这里歇歇”。天冷的时候,她用那温暖的起了皱褶的双手攥紧我的手:“看看,这小手都冻红了吧!”每当吃饭时,老奶奶总是说:“小来,你拿好面干粮吃,别见外。”当我抢先拿了剩窝窝,奶奶急地下命令,让四姑给我换成新的吃。
爷爷仪表堂堂,须髯飘胸,声若洪钟,好像小时候看过三国演义里的某个人物。爷爷经常夸我学习好,还当班里的学习委员。刚过完春节,堂屋桌子上的主匣子还没移走,爷爷突然指着问我:“你看这祖宗牌位上的字,那个写的好哇?”我仔细端详了好一会儿,也没闹清哪个写得好,只好硬着头皮说:“这个旧些的牌位上的字写得好吧”。爷爷微微一笑:“这老牌位是咱村的私塾先生点的主,可那新点的牌位是请恁们村少拔贡点题的。”哦,我们村院中的名人---清末父子二拔贡---可是远近闻名啊。这不经意间,爷爷给我上了一课。
续奶奶年轻好多,白白胖胖的,但是个盲人。除我姨夫是头前的孩子外,奶奶又生了四姑和白叔。奶奶平日里洗洗衣服,帮姨做饭烧火。奶奶整日里乐呵呵的,待人亲切和蔼。奶奶对姨没啥长辈的架子,两人和和美美像母女。
姨夫建国后就早早参加了工作,初在贾镇供销社当经理,后又改任镇政府民政助理,一直到退休。姨夫高高的个头,瘦瘦的,声音低沉而温和,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姨夫带供销社的人轮流下村送货,到我村时给我买的苹果,是第一次尝鲜呢,至今回味悠长。一九五七年,姨夫下乡整顿农业社,住我家东屋里。每次都是我把饭送过去,吃完我把碗筷收回来。上世纪七十年代,家里点灯、烧饭缺煤油,是我找姨夫想法买,救了燃眉之急。我家属随军时迁户口,姨夫骑自行车到县民政局办好手续,给我邮到部队,了却我一件心事。
老白叔比我大一岁,可上学比我晚一年。白叔小名老白,长得像奶奶,白白净净的。放了学,我俩一块去放羊,拾柴火。白叔对我很照顾,拾的柴火他背着,让我跟着就行。白叔娶了我高小同班同学韩路人王桂玲为妻,哈,女同学成了我婶子。他们育有一子一女,一家人过得很幸福。白叔在村里当了多年的红白理事会执事,为村里人操持婚丧嫁娶的事,很是受人敬重。
四姑高高胖胖的,仿爷爷的身材,比白叔还高半头。她地里的活很能干,家里的事也能操持,与姨处得很和谐。四姑小学毕业后务农,后来嫁到了李辛村,姑父姓李,在贾镇医院当医生,也是我高小的同学。你看,这同学又成我姑父啦!真是应了古人那句话:人生何处不相逢。四姑在李辛村当赤脚医生,为乡亲们看病拿药,接新生儿,深受全村人敬重。
保元哥和四姑同岁,比白叔还大两岁呢。我念高小时,他就在贾镇读中学,中学毕业后回家务农。爷爷看他不像干活的料,常教训他。一年的冬天挨了吵,跑到我家,不想回去。好说歹说地劝他,直到半夜我才送他回到家。改革开放后,他赶集卖布卖衣服。我在聊城军分区时,他还来军分区家属工厂进过两次腈纶内衣。后来他又在家养鸡,在一次去县城进鸡饲料时,不幸从公共汽车上摔下来,不治身亡。当时汽车门没有关,汽车便急速行驶,元哥被甩下车摔伤头部致死,汽车未停驶离。姨夫来聊城找我处理此事,我找到汽运公司的同学老刘,查明该车属于邯郸汽运公司及其车号,确定为行车事故并予以赔偿。
西张庄完小,西张庄姨家,我从小喜欢的地方,我永远怀念的地方,我想你们啦!
【作者简介】许钦明,山东冠县人。从小,农村儿童。读书,聊城一中。考大学,遇见。从军18载,军职正营。聊城烟草13年,干的中层。老来寻觅文苑趣,撒播花草慰心灵。
相关文章
- 每日舆情:对重要孙公司丧失控制 中昌数据雪上加霜
- 刘晓晓:自创连环缝纫操作法 大幅提高生产效率
- 松江新桥镇下属单位公开招聘!大专可报!
- 秦安县2022年技能提升(服装缝纫工)培训班开班(图)
- 保温通风伸缩软管徐州缝纫组
- 聚光灯214期|“深圳故事”演讲者赵卉洲:看见深圳设计力量讲好中国品牌故事
- 我父亲是做缝纫的缝纫平角
- 静海各乡镇缝纫女工踊跃驰援
- 七八十年代的老式缝纫机现在值多少钱呢?说出来都不敢相信
- 设计方案赛普拉斯MCU 系列一
- 买玩偶不如自己缝一个!Funzzie手工DIY缝制玩偶0基础也能做的一模一样!
-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作为历史叙事的电影
- 杰克再登央视获“全球最大的工业缝纫机制造商”称号
- 凤冈县内32家企业招聘!数千岗位在家也能就业
- 日本手工牛人把一次性纸袋做成手提包看完想学缝纫了
- 双色表皮缝纫线介绍及其模具设计与加工探讨
- 四大工程!济南这个区这样激活年轻干部干劲
- 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 阮玲斐:我从车间来响水缝纫班
- 周至人写的:母亲的手